本研究调查地点选为湖北省武汉市。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根据华顿经济研究院在沪发布的“2019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武汉位居百强城市第九名。我们选择武汉市作为调查地点,就在于武汉市处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相对落后区域的重要节点,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同时作为商贸物流中心和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武汉市还是中西部地区快递和外卖从业人员的重要输入地。因此对于研究平台工人而言,武汉市是理想的调查地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实体店几乎全部关闭,大量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均需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更是凸显出平台工人的及其重要的作用。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在无抽样框的情况下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本研究采用被访者驱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简称RDS)收集样本。我们在2019年7月-8月,采用基于社交网络的被访者驱动抽样(RDS)方式,对武汉市的平台工人(此次主要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以后将陆续涉及其他平台工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数量801份)。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对快递员(武汉市因疫情暂定外卖服务,因此对外卖骑手未追踪)进行了追踪访问(问卷数量171)。为了深入剖析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本研究还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获取质性资料。
2020年1月31日,在武汉市第五医院,快递小哥与一名医护人员擦肩而过。 新华社 资料
一、平台工人的工作状况
1、个体特征
平台工人是以青年男性农民工为主的职业。在性别上,平台工人基本以男性为主,占比91.76%;在年龄方面,平台工人偏年轻化,90%以上的平台工人的年龄分布在20岁到4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而2018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40.2岁 ;在户籍方面,平台工人主要来自于农村,占比71.54%;来源地方面,2/3的平台工人属于外来人口,武汉市内人口仅占24.22%;教育程度上,近一半平台工人的学历为高中、中专或技校。分职业类型看,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人口学特征分布相差不大,仅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略有差异。
2、入行状况
平台工人入行前的职业以工人居多。从事建筑、制造和服务的比例约占50%,从事农业的占比16.23%,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个体经营者、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等,达到8.6%。分职业类型看,快递员入行前较多从事商业服务业,而外卖骑手则多来自农林牧渔业。
亲友介绍为主要的入行方式。平台工人入行的主要方式是亲友介绍,占到了40%,说明亲友关系仍是平台工人找工作的首要社会途径;其次是网络招聘平台,约占28%;再次是老员工推荐,约14%。分职业类型看,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入行途径差不多,快递员通过亲友介绍和公司直接招聘的比例高一些,外卖骑手由老员工推荐和网络平台招聘获得工作的比例要高一些。
入行途径分布
工作自由是平台工人入行的首要原因。从入行原因看,根据图3.3可知,工作自由是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入行的首要原因,百分比为23%;其次是门槛低,百分比为14%;再次选择做快递或外卖的原因为工作不枯燥、工资不拖欠、收入高,占比均为9%。由此可见,自由灵活的工作空间和时间吸引工人加入平台经济。
入行根本原因分布
入行后面临竞争更激烈、工作更灵活、安全问题增大等状况。入行以后,平台工人面临着多重改变。最明显的变化是竞争更加激烈,占比84.39%;其次,工作安全问题变化突出,占比81.02%;再次是工作更加灵活,占比78.9%;最后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变大,比如与商家打交道的压力、时间压力、与顾客打交道的压力。分职业看,外卖骑手的工作变化均高于快递员。
入行后的工作状态变化(%)
入行后大部分平台工人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流动性较大,“挣快钱”的现象突出。如图3.3所示,进入快递或外卖行业后,平台工人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其中,快递员收入增加的比重为78.2%,外卖骑手收入增加的比重为79.4%。收入的普遍提高也是他们原因承受更大压力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平台工人的流动性较大,如表3.4所示,21.5%的人入行以后离开过本行业1次以上。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在离开次数上存在差异,在不同离开次数上,外卖骑手跳槽的比例均高于快递员。
入行后月收入变化
入行后离开次数
那些离开了快递或外卖行业的人,为什么离开后又回来了呢?25%的人表示工作比较自由是选择再次入行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工作没那么枯燥和入门简单,均占比11%;再次是暂时过渡,占比10%;最后是工资不拖欠,占比9%。按照当前工作类型来看,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再次选择入行的原因略有差异。第一,快递员认为长见识和工资不拖欠是再次入行的第二原因,其比例均为9%;相反,外卖骑手表示工作没那么枯燥是第二原因,占比13%;第二,外卖骑手因暂时过渡和还贷款而选择再次入行的比例均高于快递员。
离开后又入行的原因
3、当前工作状况
外卖骑手兼职较多,多在商业服务业。兼职外卖骑手的比例远高于兼职快递员,前者占比20.6%,后者仅为2.4%。如表3.5所示,外卖骑手的兼职工作主要在商业服务业,占比18.75%;其次是工人(包括建筑工人和制造业产业工人),分别占比8.33%、7.29%。而兼职快递员的另一份主要是制造业产业工人,占比37.5%。另外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外卖骑手的另一份工作为无业的比例较高,占比为17.71%,这是由于外卖骑手并不认为从事外卖工作是全职工作,访谈也发现,外卖骑手对外卖工作的认同不高,即便没有另一份工作,他们也不认为外卖是正经工作,而是兼职或过渡。
兼职的另一份工作分布
快递员每天派单量远高于外卖送货员,这是由两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特征所决定的。快递行业对时间的限制较为宽松,如流水线般可以持续工作,而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集中在吃饭时间,将工作时间的精确到分秒(参见图3.5)。快递员的最高派单量为500单,派单量在200-225之间占比最高,而外卖骑手最高占比在50-75单之间。
平均每天的派单量。
具体而言,全职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高于兼职快递员,全职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均值为120单,而兼职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为70单;全职外卖骑手与兼职外卖骑手每天的派单量相差不大。
一天最大派单量。
快递员比外卖骑手从业时间长,工作时间也长。如图3.7所示,从目前累计从业时间看,快递员大于外卖骑手,快递员集中在10-40个月之间,其中位值为24个月,个别快递员的工作时间高达10年之久。而外卖骑手累计工作时间在8-20个月,其中位值为12个月。
平台工人累计从业时间。
快递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高于外卖骑手,快递员工作时间集中在8-15小时,以13小时占比最高,而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集中在8-12小时,以10小时占比最高。
平台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
劳务派遣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高于农民工。平台工人属于劳务派遣的比例高,占比29.46%;然而平台工人不清楚自己是否属于劳务派遣关系的比例也较高,占比27.47%。属于劳务派遣的快递员的比重高于外卖骑手,而不属于劳务派遣或不清楚劳务派遣关系的快递员所占的比重均低于外卖骑手(参见表3.6)。与35.1%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相比 ,平台工人签订合同的比重较高,快递员占比68.65%,外卖骑手占比52.36%。
平台工人劳务派遣关系
工作满意度不高,不满多源于平台公司。如图3.9所示,平台工人对快递或外卖工作的满意度不高,快递员不满意的有23%,外卖骑手不满意的有19.7%。导致平台工人不满的来源很多,比例最高的是对快递公司或外卖平台的不满,占比50.89%,其次是对消费者或顾客的不满,占比17.16%,其余依次是工作站点、劳务派遣公司和商家,分别占比4.73%、4.14%、2.96%。当遇到不满时,平台工人主要宣泄渠道是什么呢?根据图3.25可知,找同事吐槽是平台工人遇到不满时主要的宣泄方式,其次是退出不干或忍着不说。整体上看,只有少部分快递员与外卖骑手会公开地向单位正式表达不满,绝大部分工人的维权或宣泄渠道较为隐忍。
工作满意度
当遇到不满时,找同事吐槽是平台工人主要的宣泄方式,其次是退出不干或忍着不说。整体上看,只有少部分快递员与外卖骑手会公开地向单位正式表达不满(参见表3.7)。由此可见,平台工人的工作环境相对于传统工业较为灵活自由,但是工人面临着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工作强度更大,工作满意度并不高。
表 不满意的来源与宣泄渠道(%)
二、平台工人的权益与福利
1、工资拖欠与工作伤害
工资被拖欠占比较大,拖欠时间不长。与0.84%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相比 ,平台工人遭遇工资拖欠的比重较大,其中快递员占比23.7%,外卖骑手占比15.8%。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存在在工资拖欠上存在明显差异。第一,快递公司是快递员首要的工资拖欠对象,占比47.7%,而外卖平台拖欠外卖骑手的工资的比重仅为4.4%;第二,外卖骑手首要的工资拖欠单位是工作站点,占比61.8%,快递员遭受站点拖欠工资的比重为30.7%。第三,劳务派遣公司也是拖欠工资的来源,快递员占比15.9%、外卖骑手占比26%(参见图3.30)。
工资拖欠来源
平台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时间多在3个月以内,拖欠1个月的时间比重最大,快递员占比51.14%,外卖骑手占比70.59%。工资拖欠1-2个月的外卖骑手高于快递员,而拖欠工资3个月以上的快递员高于外卖骑手。
工资拖欠时间
工作中面临的语言暴力严重。平台工人遭受被顾客辱骂、受伤、恶意点单的比重较大,分别占比34.33%、33.46%、29.46%(参见表3.8)。解决方式主要是向公司或平台反映和吐槽,分别占比56.3%、49.06%。通过找工会、上网反映情况、停工或上访、集体上访或罢工等解决方式的比重较小。
劳动过程中的伤害与解决方式(%)
职业病较多,以腰痛和胃病为主。困扰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疾病较多,主要是胃痛、腰痛、颈椎病和关节疼痛。快递员腰痛的比例最高,占比0.34%;外卖骑手胃病的比例最高,占比0.32%。
受困扰的疾病
2、车辆来源、违规与事故
运输车辆多由自己购买所得。大部分平台工人的运输车辆是由自己购买所得,占比73.91%,而公司提供的比例仅为16.85%,说明大部分平台公司不为平台工人提供生产工具。车辆自己购买和租借的外卖骑手的比重大于快递员(参见表3.9)。
平台工人的车辆来源
大部分车辆有违规被扣押过,车辆超标是被扣的首要原因。快递与外卖行业是短途运输服务行业,劳动主要是行驶在路上,交通违规与事故极有可能发生。超过三分之一的平台工人表示有车辆被扣押的情况。车辆被扣押的首要原因是车辆超标,其次是无证驾驶。
车辆被扣情况
被扣原因
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超高。据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卡车司机出事故的百分比为14.3% 。而77.4%的平台工人发生过交通事故,其中被车撞的比例最高,占比32.33%,其次是撞到车,占比26.47%,最后是撞到人,占比18.6%,说明在出行过程中平台工人主要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快递员被车撞的占比28.36%,外卖骑手被车撞的占比35.19%。
表 交通事故情况
3、投诉与罚款
被消费者投诉的比重大,调查核实比重不大。平台经济把消费者引入到劳动控制当中,消费者的评价和投诉等直接影响了平台工人的收入、奖金、职业等级等。近一半的平台工人表示被投诉过,其中快递员被投诉占比51.34%,外卖骑手占比37.98%(参见图3.14)。仅有50%左右被投诉的情况经过了调查核实。快递员被投诉后公司或平台调查核实的比重比外卖骑手高8.93%。
被消费者投诉次数
被投诉后公司调查核实
送件或送餐不及时是被投诉的根本原因,占比55.06%,其余被投诉原因从高到低依次是货物/外卖损坏或遗失、服务态度不好、未上门取件或取餐,比例分别为39.45%、18.35%、13.36%。73.16%的平台工人遭遇过不实投诉,大部分平台工人通过公司维护权益,占比31.59%。
被投诉原因(%)
是否遭遇过不实投诉
罚款是主要的惩罚方式。差评、超时、投诉等原因会被平台或站点罚款。接近一半的平台工人表示被罚过款,每次被罚款金额主要集中在50-500元之间。
是否被罚款
被罚款金额
4、社会保险
购买社会保险的比例不高,但意外伤害险购买比例高。快递员购买社会保险的比重均高于外卖骑手。不同的是,快递员的购买养老保险的比重最高,占54%,而外卖骑手购买工伤保险的比重居首要位置,占比33%。特别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两类骑手购买意外伤害险的比重较大,但是外卖骑手的比重远高于快递员。原因主要在于外卖APP设置了自动购买意外伤害险。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在社会保险购买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五险一金”上,快递员购买的比例高于外卖骑手;第二,在意外伤害险上,外卖骑手购买意外伤害险的比例高于快递员。
社会保险的投保情况
三、平台工人的日常生活
1、家庭生活与居住状况
未婚者比例较大,家庭规模较小。与2018年有配偶的农民工占79.7%相比 ,平台工人已婚者比例较小,占比54.5%。快递员已婚比例很大,占到62.3%,外卖骑手已婚接近50%。就孩子数量而言,有1个孩子的比重最大,占比68.8%,其次是2个孩子,占比29.3%,最后是3个孩子及以上,占比1.9%。对比卡车司机的家庭规模,有1个孩子的比重为37.5%,2个孩子的比重为49.8%,3个及以上孩子的比重为5.8%,可见,平台工人的家庭规模较小。
平台工人的子女数量
孩子多在老家由亲人照顾。约64%的平台工人把小孩留在老家由家人或其他亲人照顾,由配偶和老人照顾的比例均约29%。快递员与外卖骑手在孩子的照顾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快递员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比例高达43%,比外卖骑手高13%
平台工人的子女照顾
父代职业以工人为主,社会地位认知不高。平台工人的父辈职业多为工人和农民,工人占据最高比例,其中建筑工和制造业工人合计达到35.71%,农林渔业劳动者占到14.36%。整体来看,父辈职业地位较低,多为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同时也不乏向下流动的情况,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父辈职业均有一定比例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政府机关人员。平台工人的社会地位认知较低,44.8%的平台工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下层,28.5%的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仅有5.4%和5.2%的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上层或中上层。
平台工人的父亲职业分布(%)
独居比例高,自租房者比例高。从居住情况看,平台工人独居的比例较高,快递员为21%,外卖骑手为31%;其次是与配偶同住,快递员占比31%,外卖骑手占比24%。快递员与配偶、父母和孩子同住的比例均高于外卖骑手(参见图4.3)。超过一半的平台工人选择自租房,其中快递员占比51%、外卖骑手占比55.2%。自有住房和选择公司宿舍的快递员的占比均高于外卖骑手,而自租房和群租房的外卖骑手的比例高于快递员(参见图4.4)。
平台工人的居住情况
住所类型分布
2、收支状况与社会地位认知
相比农民工,收入较高,但没有底薪保障。快递员的工资略高于外卖骑手,快递员月均工资为6177.8元,外卖骑手的月均工资为5882元,与农民工月收入3721元相比 ,平台工人的工资水平较高。从工资构成来看,仅依赖派单提成的比例最高,快递员占比49%、外卖骑的占比35%;而工资构成齐全的比例不高,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比例分别为13%、12%。简言之,平台工人的工资收入高度不稳定性,绝大多数工资依靠派单提成,这也是平台工人拼命跑单的根本原因。
平台工人的月均收入
工资构成
个人消费水平高。平台工人的每月个人生活消费支出平均约2750.55元,其中快递员约2915.58元、外卖骑手约为2631.91元。租房是较大的个人支出。平台工人的平均每月租房费用约为769.1元,其中快递员765.81元,外卖骑手771.48元。
平台工人的个人消费支出
网贷成为消费压力的重要来源。近一半的平台工人有5000元以上的网络贷款,其中,快递员占比53.1%、外卖骑手占比53.4%。这反映出平台工人的超前消费行为,够了重要的生活压力源,也是驱使他们频繁流动“挣快钱”的动因。
抚养费高于赡养费。平台工人平均每年抚养孩子的费用均在两万元以上,平均每年赡养老人的费用均值在八千元以上(具体对比详见图4.7)。城市户口的赡养老人的费用最高,快递员与外卖骑手的年均赡养费分别为11208元、11740元;其次是农村户口,赡养费分别为9315元、9263元;最后是城镇户口,赡养费用分别为8942元、8528元。
抚养孩子与赡养老人费用支出
主观认知上入不敷出。平台工人认为收入不太能满足其开销,其中快递员收入不太能满足的比例为41.5%%,外卖骑手占比40.3%(参见图4.8)。因此,尽管平台工人从事快递或外卖工作后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从消费情况看,大部分平台工人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收支均衡的自我评价
四、疫情下的平台工人
武汉作为全国的疫情爆发中心,平台工人为保障城市的运转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在高感染风险中的快速流动使得各种严格隔离措施的实行成为可能。本部分基于我们在2019年7-8月对平台工人的问卷调查基础上,追踪了335个快递员,共收集了171份有效问卷。由于武汉市暂停了外卖送餐服务,因此外卖骑手不在本次追踪范围之内。
1、疫情中快递员的基本情况
家在武汉和计划春节期间工作是快递员留汉的根本原因。追踪调查发现,约64%的快递员离开了武汉。留在武汉的首要原因是“家在武汉”,占比48%,其次是“原来就打算春节继续工作”,占比22%。具体而言,农村户口更倾向于春节期间留在武汉工作。
快递员留汉情况
留汉快递员身体状况不佳。如下图所示,留在武汉的快递员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43%的留汉快递员出现了嗓子痒、干咳的症状,其次是身体无力、发高烧、得流感等症状,只有14%的人无任何症状。同时,他们当中63.8%的人进行了自我隔离,但也有36.2%的快递员没有隔离。85.7%的人未隔离还在于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也有9.5%的人在做志愿者(详见图6.2)。
留汉快递员的身体状况
未隔离时主要从事的活动
2、疫情中快递员的工作情况
快递员复工比例较低,生活所迫和参与抗疫是主要的复工原因。在171个样本中,已复工30人,未复工140人,转行1人。快递员选择工作的首要原因是生活所迫,必须挣钱,占比33%;第二位的原因是为抗疫出力,占比27%;第三是公司鼓励,占比23%;第四是公司强制要求,占比7%;最后是险中求富贵,占比3%。
快递员复工的原因
工作时间下降明显,工资浮动较大。受疫情影响,快递员的工作时间明显下降。与2019年7月相比,快递员的工作时间集中在6.5小时到12小时之间,中位值为8个小时。从累计工作时间看,快递员月累计工作时间在20-30天之间,中位值为28天。疫情期间,快递员的工资浮动较大。2019年7月,快递员的月工资在4000到9000元之间,而疫情期间快递员的日工资在50到500之间,估算其月工资在1500到15000之间。
每天工作时间
配送地点多为居民小区和医院,派单量减少。疫情期间主要的配送地点是居民小区和医院等地方,而2019年7月,除了住宅区之外,配送地点较多的是商务区。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有所减少,疫情以前,派单量集中在60-150单之间,而疫情期间派单量主要在25-100单。
疫情前后配送地点对比
从派单量看,根据下图可知,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快递员每天的派单量有所减少,疫情以前,派单量集中在60-150单之间,而疫情期间派单量主要在25-100单。
疫情前后派单量对比
客户关系缓和,工作安全压力更大。快递员疫情期间主要的防护措施是工作场所消毒、戴口罩和戴手套。快递员与顾客的关系在疫情期间有所缓解,55%的快递员认为与顾客的关系比疫情之前友好很多,20%的快递员认为比疫情前友好一些。疫情期间,快递员感受到的工作变化最大的是工作安全压力更大,而疫情前快递员工作变化最大的是工作灵活性更强。
主要防护措施
快递员与顾客的关系
疫情前后感受到的工作变化
3、 疫情中快递员的精神健康
快递员的精神健康状况较好。我们使用GHQ-12量表测量了快递员的精神健康。与2019年7月相比,疫情期间的精神健康低危人群上升了0.59%,中危人群上升了2.34%,而高危人群下降了2.93%(参见图6.10),这说明,快递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好于疫情发生前。这可能与疫情期间的工作量的减少和客户关系的改善有关。
疫情前后快递员的精神健康风险对比
4、 社会地位认知
整体而言,快递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与2019年7月相比,在疫情期间,快递员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和中上层的比重明显下降,处于中层和中下层的比重上升,这可能说明,受疫情影响,快递员的社会地位认知有所下降。
快递员的社会地位认知
*该内容来自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预印本),全文即将在中国集刊网(.cn)发布。
(华中师大社会学院郑广怀研究团队由该院一批中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组成,包括:郑广怀、刘杰、范长煜、郭之天、魏海涛、王鸥、徐晓攀、李胜蓝、朱苗、刘海娟、张心怡、幸萍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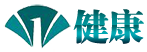
 北京紫荆医院评价好不好:前列腺的症状,每个男人都该了解
北京紫荆医院评价好不好:前列腺的症状,每个男人都该了解 G7咖啡X欧姆龙首次跨界联名,聚焦社会公益
G7咖啡X欧姆龙首次跨界联名,聚焦社会公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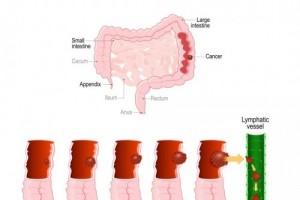 发现就是中晚期的结直肠癌,其实有办法可以避免!
发现就是中晚期的结直肠癌,其实有办法可以避免! 成都中德肾病医院主任医师--付冬梅
成都中德肾病医院主任医师--付冬梅 成都中德肾病医院首席顾问--屈燧林教授
成都中德肾病医院首席顾问--屈燧林教授 从远程急救到救命神器,迈瑞医疗用科技全方位护航体育赛事医疗保障
从远程急救到救命神器,迈瑞医疗用科技全方位护航体育赛事医疗保障 世界糖尿病日:社区药店为糖尿病健康管理助力
世界糖尿病日:社区药店为糖尿病健康管理助力 后疫情时代,高压下的职场人如何应对反复发作的头屑头油!
后疫情时代,高压下的职场人如何应对反复发作的头屑头油!